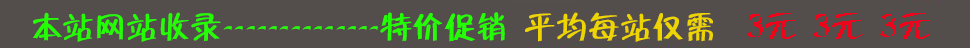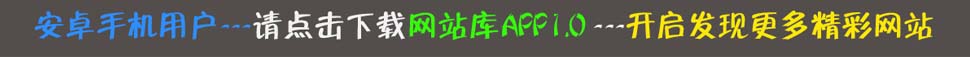2021年始,我們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產品的隕落。
有些產品消失的時候連訃告都沒人關注,其實產品也像人一樣,最怕一生平淡如水,連死都難起波瀾。
落幕的米聊,不滅的微信
在近日的微信十周年,微信公開課的“微信之夜”活動上,張小龍在回顧微信這十年時給出了這樣一句感嘆,他說:“當時絕對沒有想到,十年后的微信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對此,我自己感覺特別幸運,我想我一定是那個被上帝選中的人,因為光靠個人努力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在張小龍的口中自己,是運氣足夠好才能把微信做到如此成功,而在行業(yè)的另一邊,那個推崇順勢而為,并講出‘在風口上豬都飛起來’的雷軍卻把自身曾抱以厚望的米聊草草埋葬。
在近日米聊官方發(fā)出通知,決定將于2月1日12點開始停止賬號注冊和消息收發(fā),2月19日12點停止登錄并關閉服務器。
一個是十年猛虎回頭,一個是十年黯然落幕。
曾幾何時,米聊可能是所有通信工具中,最有希望打破騰訊的社交壟斷性優(yōu)勢的產品之一。
在十年之前,互聯網pc端用戶開始大規(guī)模朝移動端遷徙之時,QQ攥著PC端的舊票根試圖奔向移動互聯網,并想留住那群 PC端那群遷徙而來的舊人,同時來承接那些渴望在新時代尋找新需求的人。
但彼時,QQ略顯糟糕的移動化體驗,已經跟不上時代進程,似乎根本無法承載起這項任務。而這或許是騰訊主導社交工具多年來唯一的一次窗口期。
米聊看見了這個窗口,并復刻了舶來品kik通過手機號碼索引的熟人社交體系,這是當時在國內是前所未有的一種社交聚合方式。
正是因為米聊對此功能的復制,使得雷軍發(fā)現了其能為熟人社交體系提供一個全新的價值,也正是得益于此,米聊才能以單獨的產品進行發(fā)布,要知道在此之前米聊的最初定位僅是為了作為小米內部的一個通訊工具。
早于微信兩個月發(fā)布的米聊,在微信2.0版本發(fā)布之前,在與微信的競爭中一直保持著一定的領先優(yōu)勢。這種領先優(yōu)勢一直持續(xù)到微信2.0版本發(fā)布以后,張小龍對內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在內部賽馬之中脫穎而出。
直到那時,騰訊大量的資源才開始對微信傾斜,來自與qq之上人際關系的無縫遷徙,使得微信與其他同時代社交APP拉開差距的主要原因。而此時的米聊已經很難與其競爭。
有傳言,當時騰訊的二號人物與小米的林斌進行過一次接觸,張近東闡述了微信對于騰訊的重要意義,有勸小米知難而退息戰(zhàn)的意味。
是偃旗息鼓還是血戰(zhàn)到底,只能有雷軍決定,而對于雷軍而言,當年用wps血拼office,結果頭破血流的場景依舊歷歷在目,而此時以在商海沉浮多年的雷軍,或許應該更懂得權衡利弊得失,于是歷史讓我們最終看到了雷軍的選擇。
在互聯網江湖看來,米聊的消亡,既可能是小米自身戰(zhàn)略傾斜點的改變,也或許是與騰訊資源傾斜下,不對等的對壘所落下風的緣故。當用戶面臨選擇的時候,肯定會選擇使用率和實用性最高的產品。這才是米聊后勁不足,走向消亡的根本原因。
其實米聊早已完成了自己的宿命,只是當時的米聊足夠幸運,因為它出生在那個時代,時代把他推上風口浪尖,并給了他把騰訊的社交大陣撕開了一個口子的機會,這個機會米聊也把握住了,但并沒有堅持到最后。
但這足矣讓我們記住它,在它之后從羅永浩聊天寶,到字節(jié)跳動飛書,再到阿里的來往,騰訊再也沒有放過任何一個對其社交工具主導地位有威脅的玩家。
知乎回答不出悟空問答的問題
在我眼中,悟空問答是一個與知乎極度綁定的產品,像是一個“不孝”的徒弟。
而這個知乎的徒弟近日宣布,將在1月20日起從應用商店下線。
2017年,悟空問答從今日頭條中獨立出來,成為獨立App,據其早期員工透露,其產品運營方式就是在知乎上爬取問題,引入創(chuàng)作者進行回答,在其內部也是把知乎當成自身對標對象。
而悟空問答為世人熟知的方式,也是同樣因為那次轟轟烈烈對知乎進行大V挖角的事件。直到如今,悟空問答已經官宣停止運營,知乎上仍有當年被挖角的大v回憶褥頭條羊毛的那段快樂日子。也正是那次挖角,讓世人看到了當時知乎內容創(chuàng)作者,內容變現極其困難的一面。
在悟空問答初創(chuàng)之時,曾豪擲20億對創(chuàng)作進行補貼,同時在今日頭條流量的扶持下,悟空問答號稱上線五個月便以覆蓋過億人群。
而由頭條引流而成的悟空問答,其用戶屬性幾乎復刻了頭條的用戶屬性,高年齡、低學歷、低收入是他們基本特點。
而這些用戶知識儲備量大都匱乏,無法產生有質量的提問與回答,這使得悟空問答必須通過引入外部內容創(chuàng)作者來盤活整個社區(qū)問答生態(tài)。
而知乎理所應當的成了悟空問答的首選。所以我們看到了悟空問答那次引起震動的挖角事件,當然悟空問答的初衷是沒問題的,但問題在于知乎的用戶群體高學歷高收入,以年輕人群為主流人群的用戶屬性與頭條用戶的用戶屬性極度不匹配,使得這次挖角成了一次敗筆。
陽春白雪也好,下里巴人也罷,都是能組成一個完整的社區(qū)生態(tài),但要將兩者雜糅,并以一種不均衡的方式進行內容投食,就實屬強人所難了。
同時在補貼的刺激下,悟空問答也涌現出了一批通過批量生產內容,來騙取補貼的羊毛黨。
這些挖來的大V與褥羊毛的大軍在一段時間內,給予了悟空問答增加了一定數量的虛假流量,但并未為其內容社區(qū)建設添上一磚一瓦。曾有被挖去的知乎大V吐槽道“自己曾想過用心在悟空問答上進行創(chuàng)作,但社區(qū)氛圍著實堪憂,最后只得混日子拿補貼”
而當最終補貼停止,那些被挖走的大V們重新回到知乎,大批羊毛黨也同樣離開悟空問答,于是乎悟空問答順理成章的蔫了下去。
在互聯網江湖看來,悟空問答的失敗,或許是字節(jié)跳動的一次過失的資本嘗試.,同時給了互聯網之上的唯流量論、唯資本論的致命一擊,流量與資本可以創(chuàng)造出一個內容社區(qū),但卻無法賦予創(chuàng)作者留存的根本因素——社區(qū)氛圍。社區(qū)氛圍與社區(qū)流量池屬性決定了知乎大V們,在國內所生產出的內容除了知乎以外,幾乎別無二家能夠進行用戶內容匹配的流量轉化。
在此大背景下,悟空問答也在創(chuàng)作者與用戶的流失之中逐漸沒了聲響。一直到2018年7月,悟空問答被曝并入到微頭條,100多人的團隊宣布解散,一部分產品、技術負責人轉崗到其他部門,同樣也有部分運營、產品員工被辭退。
這個燒掉二十億的悟空問答已經在字節(jié)跳動內部被宣布“戰(zhàn)略性放棄”。
被放棄的蝦米
蝦米因為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沒的?
官方給出的答案是2021年2月5日蝦米關停.
而在我看來,蝦米死于2019年9月網易云宣布阿里用7億美元換取了網易云10%的股份時,
在那時蝦米就已經死了,只是這個訃告發(fā)的有點慢,慢了快兩年。
在那則訃告發(fā)出之前,蝦米一直以一種避世的方式來享受自己的死亡,
如果我們講音樂應該獨立與資本以外,那是自欺欺人,從2015年7月,國家版權局發(fā)布《關于責令網絡音樂服務商停止未經授權傳播音樂作品的通知》,要求無版權音樂作品全部下線時就注定了。在版權之下,每一個音符都是真金白銀。
而在那時,騰訊一手促成了騰訊音樂與手握酷我、酷狗兩大音樂平臺的海洋音樂的合并,組成了騰訊音樂娛樂集團(TME),這次合并使其成為了行業(yè)內當之無愧的最頭部企業(yè)。也開啟了音樂的版權大戰(zhàn)。
2017年,環(huán)球音樂的版權費初始報價僅為3000多萬美元,卻最終被騰訊付出了3.5億美元現金+1億美元股權的天價才得以拿下其三年版權。
而隨著阿里對于音樂整體發(fā)展的不確定性,蝦米在隨之到來的版權大戰(zhàn)中幾近顆粒無收,從而TME則通過版權大戰(zhàn)收獲了許多獨家版權,進一步穩(wěn)固了自身版權優(yōu)勢。
當阿里回頭再看向版權市場的時候,一切都以成定局,彼時的TME已然依靠版權優(yōu)勢占據了超70%的市場。
喪失版權基礎的蝦米音樂,對新用戶的吸引度幾乎喪失,自有用戶也在逐步流失。在面對此情此景,蝦米給出的解決方案是社區(qū)運營。
從加大扶持原創(chuàng)音樂人力度,到營造音樂社區(qū)氛圍,到音樂產品細節(jié)把控,蝦米可以說在喪失版權的基礎上能做自救,幾乎做了一遍,這些自救方案為蝦米收獲了一批忠實的粉絲,在他們眼中蝦米是他們的精神與理想領地。
但是蝦米的覆滅證實了所謂精神與理想都不如一枚孔方兄。
而最有趣的是蝦米的社區(qū)化運營并沒有拯救蝦米,卻出乎意料的拯救了模仿者網易云。可能是蝦米運氣不好,也或許是網易云版權多了兩分,而網易云懂得在版權不足的情況下尋找替代品,更愿意通過各種營銷方式不讓用戶忘記。忘了,也就沒了。
總之蝦米沒了,而宣告蝦米沒的,正是阿里給予網易云的那筆投資。
在互聯網江湖看來,蝦米覆滅的根本原因,在于阿里星球不合時宜的覆滅時間,在一段時間內似乎使得阿里對音樂領域喪失了信心,等到這股對音樂的勁頭回歸之時,版權大戰(zhàn)早已結束,口袋與兩手皆空空蝦米落寞的像個沒人疼的孩子。
阿里是擁有一個音樂夢,還是僅僅想要在音樂領域有一席之地,我們至今猜不到結果。但蝦米的消亡因素,被阿里重金入股的網易云似乎一樣不差,版權的根本缺失使得網易云的明天同樣坎坷。
但這些對于蝦米已經不重要了。
當我們已經習慣用微信交流時,忘記了米聊里的老友。
當我們刷著知乎看著新編的故事時,忘記了悟空問答里的收藏。
當我們沉浸在QQ音樂里周杰倫哼唱的旋律時,忘記了蝦米歌單中那幾十首小眾民謠。
死亡不是生命的終點,遺忘才是永恒的消亡。
對于它們而言,所有的訃告都是遲到的。